\藝穗游擊戰隊的劇場終極任務/訪談「高產能編劇」張育瀚&「超級製作人」李昀芷
小心!他們來了,你的劇場世界即將被攻略⋯⋯!有一群人,他們的名字時常出現,不一定是同個身分,可能跨團。他們帶著強烈的聲音、緊密的陣容,準備攻略你的觀眾大心。我們稱他們為——藝穗游擊戰隊。
劇場,是情感與思想交錯的現場。台上身影走過的路徑成為異時空傳送門,帶領觀眾穿越現實與虛幻。可是,藝穗的浪漫背後,團隊成員如何一起工作?推出的作品如何被看見?與觀眾的關係又是什麼?
在藝穗的新次元裡,劇場可以形塑成什麼樣貌,一切都由參戰的他們來決定。
🟢 隊員001號 張育瀚
戰力類型:高產能編劇兼導演
參戰節目:核子科技當代轉譯三部曲I《天使不獨活》──製作人暨編劇
藝穗上場經歷:
2025臺口製造《爸亡別基》蔣貞德逝世十週年紀念特演──編導
2024午夜出口《能不能和你一起憂傷?》──導演
2023耐打工作室《完全合法の喜劇教室》──編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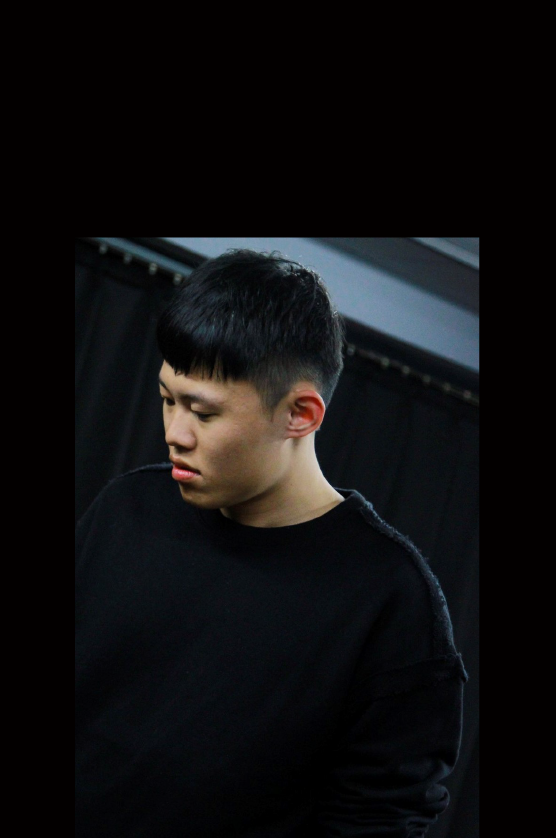
張育瀚是一位勇於探索的劇場編導,從南部踏入北部劇場,將藝穗當作實驗場,用科幻與幽默打造難忘舞台。今年除了耐打工作室的《天使不獨活》,他還為高中學長創作了《爸亡別基》。他的作品風格多元,力求零代溝,讓不同觀眾都能理解與共鳴。
對劇場的未來,育瀚保有敏銳的想像,或許正因如此,他總是全力投入製作,同時不忘與觀眾以及劇場的「同事們」保留溝通的空間。
Q:用一句話形容你在藝穗節的角色?
A:大概是「從高雄北上投資的劇場仔」吧。投資的不是錢,而是人!希望找到未來還能一起創作的夥伴。藝穗節對我們而言,是還沒能做大製作前最理想的試煉場。
Q:聽說你在藝穗遇過一件「靈異票房事件」?
A:對,《能不能和你一起憂傷》那次,劇情設定是外星人附身在演員身上,我們讓演員真的帶著這個設定去做田調,問身邊人對「憂傷」的看法。
有場票房一直卡在只賣出一張,我們就開玩笑說:「那就當中元普渡場吧。」結果隔天,那張票退了……
後來演員從台中回台北,照例去家裡的師傅那收驚。師傅先嘆一口氣,問:「最近有演戲嗎?是不是跟附身有關?」
他說,我們排練時吸引了不少好兄弟來看,還有生前是「同行」的,想附身給我們筆記。大家聽完全跪,立刻道歉:「沒有要普渡場!」結果神奇的是,那場在這之後終於陸續賣出票券。

2024臺北藝穗節 午夜出口《能不能和你一起憂傷》劇照(攝影|Grace Lin)
Q:可以描述一下你的創作流程嗎?
A:第一步是找製作人討論規模,先有市場考量;第二步是先定演員再寫劇本,因為我自知寫得快,也想讓角色貼近演員本身;第三步是認識場地,尤其觀眾距離。
南部小劇場比較多,培養出一種「鬆」的表演感,這對我設計表演和空間互動很有啟發。
Q:《天使不獨活》是怎麼誕生的?
A:來自盜火劇團的華文LAB劇本工作坊。題目是從新聞發想,當時我找到臺灣核武發展人物張憲義的新聞。
他到底是叛國還是救人?他的選擇讓我想到,劇本本質就是角色一連串的抉擇。於是我把它轉成一個科幻故事:世界出現名為「天使」的生化武器,原本用來治癒癱瘓,卻被改造成毀滅型武器。製造者需要決定,要不要讓它繼續?
臺灣科幻的劇作本來就比較少,比起燈光效果和舞台,我決定用臺詞和氛圍創造那種龐大的感受。

排練中的張育瀚
Q:藝穗節的舞台,跟一般劇場有什麼不一樣?
A: 我覺得藝穗的體制本身就不是為了賺錢設計的。進入這個平台的作品,通常都還不是終端製作,也不可能期待大賺一筆。藝穗的設計本來就是讓創作者有實驗與嘗試的空間,而觀眾也帶著「這裡是可以 try 的」既定印象。因為空間小、觀眾數少,創作者反而能與觀眾保持理想的親密距離,第一時間就能收到最真實的回饋。
既然目標是獲得回饋,我們甚至放棄了過去「按讚送禮」的方式,改用請觀眾填寫「全民瘋藝穗」評論來換紀念品。這個改變成功增加了觀眾的參與,也讓我們收穫更多想法和建議。
2023臺北藝穗節耐打工作室《完全合法の喜劇教室》
Q:最後,如果讓你預言劇場的未來?
A:我最怕的,是劇場變成「買高價票」成為炫耀權勢的象徵,觀眾其實看不懂,也不在乎內容。那是我能想像的最恐怖未來。
至於為什麼我還留在劇場?因為小時候,我遇到一群不同年齡的人,一起完成一件事。劇場對我來說,是最重要的交際空間。我不想讓這件事在我手上消失。
🟢 隊員002號 李昀芷
戰力類型:把工作當充電的超級製作人
參戰節目:藝穗前夜祭:達秋劇團《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》+達秋劇團《天亮前的愛情故事》+小嶼造夢所《呼叫太空急救中心》──製作人
藝穗上場經歷:
2024達秋劇團《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》──製作人
2024小嶼造夢所《小房間的末日》──製作人

如果說導演是劇場裡的夢想家,那麼製作人就是能把夢放進時程表與 Excel 表格的人。
李昀芷,大學還沒畢業就開始接案,現在手上同時跑著七、八個製作。聽來瘋狂,但她卻笑著說:「工作是我的充電方式。」
我們和她聊起藝穗節,聊起製作,聊起那個看似龐大卻充滿樂趣的「高壓現場」。

2024年臺北藝穗節《小房間的末日》演員甄選日
Q:今年你帶了哪些作品參與藝穗節?你現在的狀態是?
A:這次同時有三檔戲!
第一檔是《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》,去年得獎後再製,票很快就完售了。
第二檔是達秋劇團的《天亮前的愛情故事》,之前曾經在「去他媽的讀劇節」試過水溫,聊的是當代愛情的速食樣貌。
第三檔則是小嶼的《呼叫太空急救中心》,在校內讀劇時迴響不錯,這次將在思劇場演出。
達秋的戲目前都是用黑色幽默包裹沉重議題,小嶼則偏可愛、夢幻。不過,兩個團都還在初創立的階段,我們希望能先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作品,還不急著被市場定義只做某種風格。
Q:身為製作人,你在藝穗最難處理的狀況是什麼?
A:最難的是預算~觀眾基數小,成本要壓到最低。這次兩齣戲我們都選擇比較容易有共鳴、好接近的愛情主題,我們是有意識的要把作品推到不常看戲的年輕人手上。
但我覺得藝穗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:觀眾會包容可能的「踩雷」,而劇團也默許觀眾預設踩雷。這份默契,反而讓創作者更自在去嘗試,也讓更多的對話、驚喜發生。
Q:回顧這幾年,藝穗節對你來說是什麼樣的存在?
A:我從大二開始接案,校內也常擔任執行製作,很喜歡像專案經理那樣,從 0 到 100 把大家兜在一起。藝穗給了我這樣的場域。
和學校的大型學期製作相比,藝穗的空間和時間都比較小,但觀眾包容性高,氛圍很不同。那是一種「小規模卻高密度」的實驗空間。


2024犇藝獎《關渡顯影祭》策展人結案報告
Q:你同時跑三檔戲,還有其他案子,怎麼調適這樣的節奏?
A:其實我目前大概同時有七、八個案子在進行,但它們各自的時程不一樣,有的還在開發,有的已經在結案,所以不會真的同時全部壓在一起。
對我來說,工作其實就是充電。因為我喜歡跟人溝通,也喜歡發現問題、解決問題。每一個案子都讓我更了解自己,也讓我找到適合的合作模式。像是我發現如果我比較能接受一開始就談清楚的案子,所以就會先把條件和需求先講好,後面能省掉很多磨合。
Q:藝穗製作跟業界製作最大的不同在哪裡?
A:最大的差別就是「合作的氛圍」。業界有合約、有責任,有時候就是「死線到了」。但藝穗預算有限、大家彼此體諒,我更常問的是:「有什麼我能幫你?」這讓我學會調整領導方式,不同的人,就用不同的節奏。

2024年臺北藝穗節《一個外送員的21種死亡方式》前台側拍

思劇場進駐活動上作為品牌暨節目經理致詞
Q:未來,你最希望在藝穗挑戰什麼?
A:藝穗少見的一點是:製作人不一定要當領頭羊,而可以跟朋友一起用力地玩。這是我很珍惜的。
我希望未來能在藝穗有更多新型的行銷嘗試,幫助劇場破圈。票價的問題也很現實,台灣劇場要走向更親近觀眾的定價,還需要更長遠的開源、節流。
短期來說,藝穗幫助小團能定期產出,成為發展作品的關鍵,慢慢養成能獨立製作的能量。長期來說,好處會是跟場地的更多媒合,打開更多不一樣的合作可能。
Q:最後,一句話送給藝穗?
A:藝穗是一個「踩雷友善」的地方,對觀眾和團隊都是!
歡迎來看戲,而且歡迎「任何人」來看戲,開箱這些節目裡獨有的浪漫。